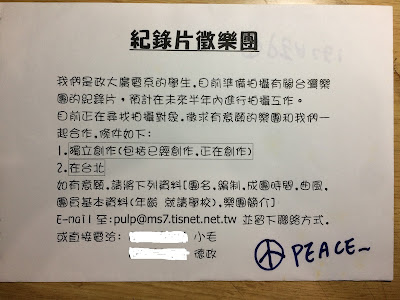濁水溪公社兩張專輯與紀錄片上線水晶頻道(三)
從【爛頭殼】看濁水溪公社 羅悅全
濁水溪公社一向以現場表演猛爆聞名
濁水溪公社成立於1989年,2020年解散。一直被視為台灣最重要的地下樂團。他們在水晶唱片一共出版了兩張唱片,分別是「牛年春天吶喊」現場錄音(1997)與「臭死了」(2001),同年,水晶還發行陳德政、毛致新為他們拍攝的紀錄電影「爛頭殼」。
慶祝濁團三張作品在水晶頻道上線。我們分別邀來馬世芳、陳德政與羅悅全三位台灣獨立樂圈名筆的三篇稿子,大家看看這三位卓富盛名的文化人如何看濁水溪公社。
從【爛頭殼】看濁水溪公社 羅悅全
本文作者 羅悅全是 「立方計劃空間」成立者之一,過去曾任職資訊網路公司,亦長期關注台灣地下音樂、實驗音樂與聲響文化等議題,曾參與編著與翻譯數本相關書籍。「立方計劃空間」以 造音翻土──戰後台灣聲響文化的探索」展覽獲得「第十三屆台新藝術獎」。羅悅全並著有「秘密基地:台北的音樂版圖(Since 90\)」(商周出版)、翻譯有「 迷幻異域:快樂丸與青年文化的故事」(商周出版)
本文作者羅悅全。羅悅全提供
紀錄片工作者吳耀東在數年前曾拍過一部得獎的紀錄片《瑞明樂隊》,紀錄一群抱持另類想法的青年帶著樂器遁入某山區的無人破屋中,過著公社式的生活,他們認為財產不重要,和朋友在一起過著自由的生活,每天玩樂團,才是生命的重心。但是他們的熱情沒有維持很久,團員每天湊在一起卻玩不出什麼結果,沒有目標,加上家庭壓力,團員一個個離去。最後一個鏡頭是,拍攝者找到失蹤已久的某團員,追問:「你還想繼續玩團嗎?」他苦笑不語。
《爛頭殼——濁水溪公社影像紀實》也是一部台灣玩團青年生活寫實,但紀錄內容不是默默無名的樂團,而是在台灣地下樂團中享譽盛名兼臭名的濁水溪公社。
「爛頭殼」紀錄片,陳德政、毛致新製作,水晶唱片出版(2001)
雖然這是部樂迷拍給樂迷看的紀錄片,但即使觀者對濁水溪公社毫無所悉,也可以從片中得到某程度劇情片的趣味,順便大概了解一下台灣地下音樂的風景:一支頗有名聲的樂團,在新專輯發行的前後,漫不經心地練團(卻興致勃勃地策劃每場表演的「行動劇」)、全台巡迴表演,最後的高潮是在重要團員退出的情形下,臨時找來一名吉他手參與「春天的吶喊」的舞台暴力行動(毀掉九把吉他!)。但在激情過後,這支樂團又因為二名團員必須入伍而暫時散解。
濁水溪公社自 1990 年成立以來,一直是台灣地下樂圈中最受爭議的樂團,打開始就把「態度」擺在「音樂」前面,踐踏前人奉為圭臬的「搖滾精神」,發表的宣言幾乎比歌詞還多,每場表演都以混亂收場。但諷刺的是,這支不把音樂瞧在眼底的樂團,卻是現在台灣玩團青年心目中最重要的團體之一。從今年 1 月 19 日舉辦的向濁水致敬演唱會就可以看出來,在台灣能夠被這種陣仗對待的搖滾樂手,除了紅螞蟻、薜岳之外,也只有濁水溪公社了。
許多支持者認為,濁水溪公社最大的魅力來自於他們語不驚人死不休的坦誠,以及為人所不敢為的現場表演,為現今飽受壓抑的台灣中產階級青少年提供最佳的情緒宣洩出口。但另一方面,濁水溪也是充滿矛盾與衝突的樂團,這樣的矛盾在交互衝激之下,也成為他們源源不斷的創作能量。
砸吉他式的暴動演出是濁水溪公社的特色。圖片截自「爛頭殼」影片。
首先,從作品上來看,雖然口口聲聲說自己的音樂能力很爛,但他們歌曲的悅耳流暢卻是少有樂團可及;雖然企圖顛覆所謂「搖滾精神」,但他們的直言不諱、音樂的粗糙原始與爆發力卻被樂迷認為是「真正的搖滾精神」。在《爛頭殼》中,也處處可看到這樣的矛盾。
一般認為,濁水溪是關懷台灣底層人民生活的樂團,但很明顯,他們樂迷結構卻不是他們所關心的「底層人民」,絕大多數是擁有中上學歷的都會知識青年,而且,若仔細看看他們歌詞與表演,那樣尖酸戲謔的手法也很難說是一種「關懷」。
另一種常見的看法,濁水溪公社在政治意識型態上堅決地主張台獨,基本上是沒錯,但在《爛頭殼》裡一段於二二八紀念公園舉行的「 Say Yes to Taiwan 」演唱會中,小柯與左派演的「建國」與「哈爾濱大陸妹」行動劇,看起來卻像是嘲諷某種台灣人的阿 Q 心態:上了大陸妹就是台獨建國的精神勝利。甚至在練團室準備演出時,還有這樣的對話:
「明天是二二八什麼的,何必要應景,全部唱跟二二八沒有關係的……,唱那些,獨立又不會成功。」
「唱梅花?」
「原來我們是假左翼,真急統。」
「不行啦,你這樣唱,人家還以為我們是諷刺,一定達不到那個效果。」
這裡並不是要指出濁水溪公社的表裡不一,其實以上的表現正是一種表裡如一:抱持著理想,卻又對理想的不可及和現實狀態保持無力感和自嘲,不正是濁水溪公社一貫的態度?就像〈社會主義解救台灣〉一曲中,在激動的口號和刺耳噪音裡,卻是喃喃自語:「老闆我要放假……」。
從這點來看,與其說濁水溪公社是「關懷底層人民」、「堅決主張台獨」,不如說,底層人民的生活和台灣懸而未決的政治地位等題材,在他們的作品裡,是種身為台灣人的複雜感情:壓抑、憤怒、無奈、荒謬,對眼前亂象一方面期待改變,另一方面卻又自在地於其中翻攪。他們以黑色幽默呈現出所處環境的五味陳雜坦誠地表達自身的處境,正深深地敲進台灣搖滾迷的心裡。
曾有人說:做一個好樂團要夠混帳,濁水溪公社就是這麼混帳到骨子裡的好樂團。
VIDEO
有人說濁水溪就是個混帳到骨子裡的好樂團。
不過,濁水溪 的原動力,也可能成為讓自己步入毀滅的因子。比起無疾而終的「瑞 明樂隊」,濁水溪公社當然是有搞出名堂,得到一定的成就,但是他們所面臨的問
題與瑞明樂隊並無二致,如果玩團最好的目的是「沒有目的」,那沒有目標的路要
走到何時?如果一次又一次的暴動演出將他們推向高峰,那下面的問題是,如何超
越?或是如何下來?
在《爛頭殼》中,我們也看到濁水溪面臨的問題。失控混亂的場面,一向是濁水溪公社現場表演追求的目標,他們不止一次在訪談中表示,希望把失控暴動玩到極致。而在《爛頭殼》開頭總統府前廣場跨年晚會表演中,團長小柯在欣喜於「假如真的在那個廣場,真的太酷了」的同時,也希望「失控」能夠在「控制」之內,結果未如預期,左派依舊失控地將砸毀的電吉他扔入人群中,造成一位女孩受傷,家長怒氣沖沖至後台問罪,小柯狼狽解釋:「其實我們只有一個人在丟……,所以我也在找他。」之後轉移陣地到「地下社會」演出,小柯說:「還是回來這個小地方比較快樂。」
走到一定的地步,不再是場遊戲,濁水溪內部也產生了危機感,片中鼓手 Robert 頻頻抱怨
「現在不行了,左派也結婚了,大家的感情也穩定了。」
「都這麼大的人了,還在玩小孩子的遊戲,幹,也不想想你們幾歲了。」
「我看我們快完蛋了,真的,你們快被時代淘汰了……,現在人家都在流行什麼,你們還在幹嘛……人家是可憐你們,看你們撐了這麼久,當做是一種『民俗技藝』在看你們,從來也沒有人喜歡過你們啊。」
要如何將「失控」轉為「可掌控」?這不僅是現場表演的問題,也是樂團未來方向的問題。片中沒有提到一個重要的事件,濁水溪公社在「 Say Yes to Taiwan 」演唱會之前,曾對《破週報》的訪問發表政治極不正確的言論:「我們的理念就是暴力門派的,我們恨不得就是組織自己的游擊隊,我很就是恨不得就是跨過那個台灣海峽,過去殺幾個那邊的……去福建……殺幾個中國人,就算自己死了,反正我們命就是這麼爛,活著也沒甚麼意義,乾脆就是去殺幾個他媽的燒殺擄掠一番,強姦,姦淫幾個中國人,然後就是幹一聲,那真的實在是太爽了,這輩子就實在是太酷了真的是,殺幾個馬家莊的啦,甚麼趙家村的啦媽的,抓幾個女的出來幹,幹他媽的雞巴,幹,可以呀。絕對可以,生命就是這樣子,跑來這邊唱歌其實就沒甚麼了不起了啦,對我們來講,生命就是這麼渺小了。」-《破報》復刊 146 號
諸如開到大陸妹的表演語言曾造成論戰。圖片截自「爛頭殼」。
其實這也是一種「失控」,濁水溪似乎相信無論他們怎麼惡搞、怎麼胡說,都會被認為:「反正濁水溪就是這樣」,擺爛到底就可以得到言論免責權。但這段言論失控立刻受到嚴厲的撻伐,進而形成樂迷和《破報》間的一陣對罵,這和電吉他砸傷女觀眾一樣,不是他們想看到的局面。
如果他們拒絕進一步思考這個問題,那也就只能「回到小地方比較快樂」。
差不多就在這陣風波之後,同時也是這部紀錄片第一版公開發表前沒多久,左派離團了。其實在這部片開拍前,原任貝斯手劉柏利也正好離開,由阿熾入替。《爛頭殼》片中並沒有仔細處理二位重要團員為何離開,我們在片中看不出任何線索,只能大概猜想,或許是「左派也結婚了,大家的感情也穩定了」。
多做臆測也沒什麼意思,對樂迷來講,只希望濁水溪公社能如片中結尾的對話, Robert 對小柯說:「我們當兵的這兩年,你就寫歌嘛,等退伍以後剛好出新專輯。」兩年以後,台灣的地下樂圈或許有變,或許沒變;台灣的政治社會或許有變,或許沒變;濁水溪公社或許有變,或許沒變……,世事無常,一切都很難說,就像十多年前沒人認為濁水溪公社能玩到 21 世紀。